苏北偏北的苦楝树
——读孙爱雪《流浪的女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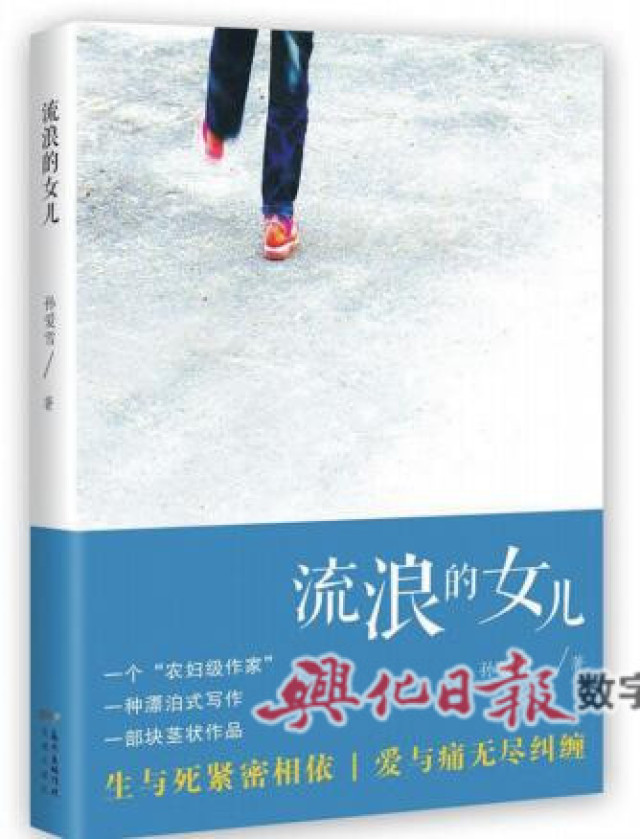
□庞余亮
什么样的泥土会长出什么样的树。比如苏北偏北的黄土上不会长出牡丹,也不会长出荔枝。它们经不住反复改道的古黄河的折腾。在这块土地上,只有坚韧而耐烦苦楝树,如孙爱雪一般坚韧而耐烦的苦楝树。
这是一枚浸透了黄连的苦胆。瘸腿的母亲因为难产而死。被人称之为绝户头的聋父亲在穷困中将女儿孙爱雪拉扯长大。偏偏这女儿又是敏感的。每一缕风,每一道阳光,每一个声音,都会令这棵苦楝上的小叶子颤栗不已。
颤栗,是对麻木的反抗。可又怎么能不麻木呢?在饥饿的胃前,每种食物都是那样的稀缺,又是那样的不可想象,就像巨大而沉重的石碾,碾过了那些瘦小的胡萝卜。再瘦小的胡萝卜也会交出内心的汁液。黄澄澄的汁水浸漫过干枯的石碾,在饥饿的石碾旁,那个饥饿的女儿不能呼唤,因为她的父亲听不见。而那些乡亲们也都在各自的饥饿中。
我记得这样的饥饿,也记得那座饥饿的孙庄,每家每户在昏黄的日子里,每个人的脸都是灰暗的。因为是女儿身,她属于孙氏家族,又不属于孙氏家族。因为贫穷,失去了妻子的聋父亲只剩下了彷徨和徘徊。有两个特别不能理解又是特别心酸的镜头,没有燃料的父亲为了给女儿烧一顿热饭,竟然拆下了多年跟随的囤。在一个雨季中,父亲锯掉了支撑房屋的屋梁点火烧饭。这不是破罐子破摔,也不是拆东墙补西墙,而是一个父亲无奈的爱。
没有什么更多的物资生活,一口井,一只蜜蜂,她在孙庄发现属于她的“针尖上的蜂蜜”,但在那样的歧视和耻辱中,在近亲的白眼和冷漠中,她被窘迫追赶,被贫穷鞭打。为了寻找一张可以休息的床,她几乎穷尽了一个小女孩所有的智慧。人间的温暖和寒冷,都在哺育这棵小小的苦楝。她内心的清寒几乎可以构成一万个冬天。
但她依旧没有绝望,就像她的父亲在不断都修屋。即将倒塌的屋里,永远有一盏墨水瓶做的油灯。油灯坚定,活着的信念坚定。她开始了求学和奔跑。她的学生之路更为狭窄。但她爱书,爱书本中的光亮。从初中到高中,她几乎记得每一个日子每一张脸,甚至在疾病中吃下的每一颗药。但苦楝树依旧葱笼,比如她的文学梦,和那些呵护她的文学老师们,很多素昧平生的人成为了她的春天。
但困顿和厄运继续,就像1988年,20岁的她开始成为一个小工人。但命运的雪花带着倒春寒扑向了这棵刚刚长高的苦楝树。聋父亲生病。在那个一分钱也难死英雄汉的日子里,她借了一次又一次钱,仿佛是在赌气,为了从疾病手中夺回她唯一的父亲。她抵达了1988年,可1988年又是那样的难以逾越。她甚至赌上了自己的婚姻。好在她依然站着,站在苏北偏北的孙庄,像一枚苦胆高悬。
这么多年过去了,她没有忘记读书,没有忘记写作,没有忘记她的生长。她在一望无际的奔跑中,将每一刻窘迫和贫困化成了星星点点的苦楝花。这个流浪的女儿,这棵来自苏北偏北的苦楝,终于长成了一棵可以庇护她的母亲父亲的大树了,就像她用这本28万的自传,为苏北偏北写出了新标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