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与现实的碰撞
理想与现实的碰撞
——访里下河文学·星书系小说集《青草》作者易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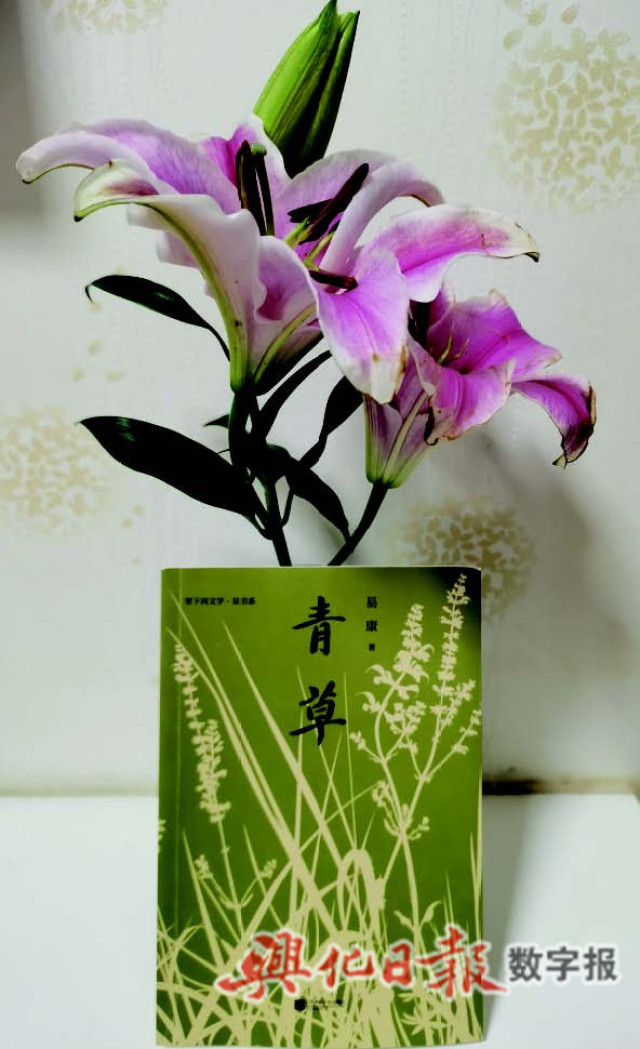

□文/ 沈倩
易康,江苏省兴化人。1961年生,现执教于兴化市板桥初级中学。工作之余以读写自娱。2012年开始先后在《花城》《上海文学》《大家》《山花》《雨花》《作品与争鸣》等杂志发表中短篇小说及作品专辑。中篇小说《青草》荣获2015年—2016年度郑板桥文学艺术奖,小说《毕业生》荣获泰州市第三届稻河文学奖小说奖,小说《恶水之桥》入选中国小说学会2018年度中国小说中篇小说排行榜。
兴化历史悠久,文化氛围浓厚。催生当代“中国小说之乡”和“兴化文学现象”,兴化作家已然成为里下河文学流派的中坚力量,引起中国文坛持续地关注。兴化本土作家易康的小说创作立足于传统文化,又有现代主义的倾向;既根植于现实,又有对历史的思考。近日,他的小说集《青草》入选里下河文学·星书系并出版。小说集《青草》选刊了《普鲁士蓝》《暗处》《风·尘》《情·探》《回家》《青草》《枪替》《恶水之桥》《玉骨》9部作品。为了探寻小说集《青草》背后的创作故事,本报记者特地采访了小说集《青草》的作者易康先生。
记者:小说集《青草》收录了您的9部作品,为什么以其中一部作品《青草》的名字来命名整本书呢?原因是您曾经说《青草》是您的精神自传吗?
易康:《青草》是我个人比较偏爱的小说。在这则小说里,我做了一些形式上的尝试,在写作过程中几乎是将自己完全放开。那过程虽然艰辛,但也比较快乐。另外,《青草》中的人物大多是平凡的人,甚至是平庸之辈,而我作为一个乏善可陈的作者,跟他们倒有几分相似。所以思前想后,就决定以“青草”来命名这本书了。说它是我的精神自传,是因为我与小说中的人物有过一样的困惑与挣扎,因而流露出的情感也比较真实。
记者:小说集《青草》收录了9部作品,您觉得这9部作品有什么不同特点?或者说表现了哪些不同的主题?这9部作品又有什么价值意义?
易康:《青草》收录的9部小说,有写古代、民国,也有写当代的。《青草》《玉骨》相对抒情意味浓一些,《枪替》《回家》比较写实,《暗处》《恶水之桥》在叙述上有点前卫。我还处于学艺阶段,所以写出来的文字谈不上价值。尽管如此,我还是渴望这些小说能带给读者一些阅读上的愉悦,进而有所感有所思。
我一直把对人性的探究作为写作的主要目标。《暗处》写的是一个孩子对真相的追寻,而外部的力,使之戛然而止;《玉骨》则以我们兴化的李园作为背景,其中的人物、故事虽然纯属,但无疑寄托了我对这座建筑的情感与遐想。《风·尘》这部小说以大家所熟知的杜十娘为主角,我没有要颠覆这个经典的意思,只企图更多地从人的角度来解析。杜十娘投江自尽的时候才十八九岁,这是现在高中生的年龄,而她选择李甲,很是耐人寻味。
记者:小说集里的9部作品,您觉得有没有共同点呢?
易康:虽然在时代背景和选材上有所不同,但我都力求写出人的企盼。我们的生存环境也许还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我们必须活出希望,并为之付出努力。我的小说在表达方式上多少带有一些现代主义的痕迹。我迷恋上文学的时候,恰好是改革开放刚开始,一些西方现代主义的作品陆续介绍到中国。而我作为一个有猎奇心理的青年,很快被这种特殊的方式所吸引了。我有时候想,如果我早生十年,或晚生十年,也许是一个坚定的写实主义者;但我有时候又觉得,选择什么样的表达方式,恐怕也不是仅凭意志就可以做到的。
记者:您曾经说过,一个作家最重要的是情怀,这也是您一直追求的,能具体说一说吗?
易康:这话其实是毕飞宇先生说的。原话是这样的:情怀才是(作家)最重要的才华。因为这话对我触动很大,所以才常挂在嘴边。我觉得一个作家应该有对人的命运的关注,把对人的研究成为其生活的一部分,做到时时留心,处处留意,这种积累也应该成为情感的积累。小说是形象思维,但也是情感的抒发。回过头想,我之所以喜欢《喧哗与骚动》《了不起的盖茨比》《暗店街》这类小说,一定程度上是被其浓郁的抒情意味所吸引。作家也许应该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一个梦想家,他们的作品也许来自理想与现实的碰撞。
作家艺术家要有悲天悯人的情怀,中外的著名作家虽然在文化背景、生存环境、性格特征各不相同,但大都具有这样的情怀。我是这么认为的。
记者:文学和商业,您觉得两者的关系应是怎么样的?在当今社会应该要保持怎样的平衡?
易康:商业对于文学来说,也未必全是负面的,有些伟大的作品,如《尤利西斯》等,就仰仗了商业的运作。但这的确是一把双刃剑。一些过度的商业炒作,对文学的伤害那是肯定有的。我坚持认为,在商业社会里,写作会带给我们一些名和利,但我们不能只为了名利而写作。坚守我们的精神家园,坚持文学艺术的纯粹,这在商业社会显得尤为重要。我们既要有“文章千古事”的信念,又要有“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刻苦和执着。而作为读者,当然要有一些辨识度,要能避开那些有商业炒作嫌疑的书籍,选择适合自己的经典读物。
记者:有人说“现在的人不爱文学”,对这种看法您持有什么态度?
易康:我不太赞同这样的观点:现在的人不爱文学。我常在“豆瓣”上看到一些年轻人在表述自己的阅读认知。我很喜欢那些表述,甚至认为他们的读后感,可能比评论家的专业论述更有意义。由于文化的多元和网络的发达,阅读纸质书的群体自然不如我们年轻时代的那么多,但绝不等于现在的人就不阅读文学作品了。在我工作的学校就有众多的文学爱好者,而且其中有不少是理科老师,他们的阅读不带任何功利性,完全出于爱好,完全是在享受文学带给他们的乐趣。我想,这样的现象肯定不只限于我所工作的地方。
我曾有幸被拉到一个阅读写作的微信群,在群里大多数是中青年作家、评论家和编辑。我能深深地感受到他们的勤勉、专注与智慧,也由此看到中国文学的未来。“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年轻一代定能成为中国当今文学的强劲“后波”。
记者:您在创作的时候,有没有遇到瓶颈期,是如何突破的,可以聊一下吗?
易康:我好像一直都在瓶颈期,每写一篇都觉得力不从心,都充满了自我质疑自我否定。我一直在写作中苦苦挣扎。由于长期处于这种状态,所以不得不想办法寻求心理上的排遣。我常用的方式就是,将过去清零,告诉自己现在从零开始,这样我就可以轻松一些。
记者:就文学影响方面,聊一聊您父亲给您带来的,以及您给您儿子所带去的?
易康:我父亲学的是美术专业,在写作上也许是个外行,但他有时也看一些小说,他很喜欢白先勇、汪曾祺两位先生的作品,他觉得他们都很有学问。他的这种“学问论”,使我认识到写作需要学问,而小说创作本身也应该是一门学问。
父亲对我影响最大恐怕还在价值观上。他认为艺术和文学是神圣的,像施耐庵、陈老莲、莎士比亚、达芬奇、贝多芬都是与日月同辉的人物。他经常向我灌输这样一个观念:一个人可以不做官不发财,但不能没有文学艺术方面的素养,缺乏知识是极为可耻的。有意思的是,父亲在发现我喜欢文学后,便千方百计加以阻扰,这应该是出于对我的爱护吧。更有意思的是,若干年后我也用同样的方式对待我的儿子,我很希望他能成为一个理工男,然而最终事与愿违,很遗憾,他跟我一样成为了文学爱好者。
记者:您现在正在创作有关什么主题的作品,可以透露一下吗?
易康:我一直梦想着将传统叙事文学的一些因素融入到我的作品中,虽然力所不逮,但我一直努力这么去做。由于懒散和才学的缺乏,我的写作没有什么规划,尽管如此,我还是渴望写出明晰而又有深度的作品。我不知道自己在写作上能走多远,但我会坚持,并认真地对待我所写的文字。也许我终究会回归写实;也许会战胜懒惰,写出长一些的小说。当然,这只是我的愿望,能否实现,还要看我是否有勇气有毅力克服自身的弱点。
记者:您经常在朋友圈与大家分享一些书画作品,您觉得书画作品与文学写作之间是不是有联系?有考虑把两者结合进行创作吗?
易康:我在少年时代曾经随父学过一段时间的美术,美妙的艺术作品所带给我的极大的审美愉悦至今难忘。我曾经翻看过像《阿波罗艺术史》这一类的书籍,从中感觉到,那些伟大的艺术家与其算是在呈现,不如说是在讲述。我一直笨拙地去探寻那些伟大作品背后所隐含的故事,因此我觉得绘画作品与文学作品有本质上的共同点。法国著名作家西蒙、萨洛特就曾从绘画中获取写作的灵感,而绘画大师巴尔蒂斯则将我们的《东坡诗集》《西游记》作为艺术创新的源泉。
也许有一天我能写出像样的小说来了,那时我便会让自己放松一下,写点关于名画赏析的随笔。我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记者:对于目前兴化地区文学爱好者的整体写作状况,您有怎样的期待?
易康:自从“毕飞宇工作室小说沙龙”开办以来,我们兴化的本土作者享受着令人羡慕的学习上的机会和创作上的扶持,这在国内的县级市里是十分罕见的。回顾我这几年的写作状况,竟然毫无长进,内心充满愧赧。我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格对兴化的基层写作状况做一个评判,只是觉得,我们的创作水平还有比较大的提升空间。
我恳请我们兴化的同道们,静心读书,努力创作;团结一心,共同进步。不可妄自菲薄,也不可自以为是。不要将文学当做名利场,不要动不动就以作家自居,你我都还不能算作家,甚至连个半吊子文人都不是;不要动不动就将一些粗陋的文字到处乱贴,即使为了生计,也要适可而止。对文学要有敬畏之心,要有谦卑之心。写得不好,要有羞耻感。惟其如此,我们才能更好地服务于读者大众,不负各方的大力扶持,不负毕飞宇先生一次次不厌其烦的悉心教诲;也才能有所提高有所长进,为兴化本土的文学事业的发展尽心尽力。













